 中文
中文

已經工作三年的王寧逐漸感受到「壓力上湧」——她盯著電腦屏幕做報表的思緒越來越難以集中,站在打印機前,她會突然看到垃圾桶裡丟棄的文件,然後忘記自己本來要印刷哪一份材料。
今年3月前,她以為這只是壓力過大導致的精神恍惚,直到她有一天在小紅書上刷到一個博主在介紹「ADHD」這個名字——影片博主本人早已在海外醫院確診,但對於當時的王寧來說,這還是很新鮮的一種精神類疾病。
博主本人在影片裡表現得非常活躍可愛,在社交媒體上廣受好評,王寧在這個影片裡感受到了那個和自己朝夕相伴且常常給自己帶來困擾的思維模式,一切指向ADHD的臨床表現:思維跳躍,不連貫,難以集中,多個聲音搶奪大腦指揮權,多線程並線共行。
「看到毛絨地毯,想起小貓的毛發,於是想到了虐貓事件,然後我開始哭,」王寧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直到我開始刷到一些ADHD相關的帖子,我才知道我不是一個怪人。」
ADHD全名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常見於青少年,年幼時即可通過醫療手段確診並加以矯正。任何心理障礙、疾病都是正常心理波動范圍外的極端狀態,對生活造成影響了才被稱為「極端」或障礙。

中國對精神類疾病科普的缺乏導致污名化現象嚴重,間接導致一些精神障礙的確診率並不高,ADHD也是其中之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流行病學調查數據,ADHD的平均患病率在2.8%左右。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推算稱,中國至少有2520萬人被ADHD影響生活——但確診率低,知名度相對低,導致民眾普遍對這個精神障礙並不熟悉。
澳大利亞健康專業監管局(AHPRA)注冊心理學家楊欣在接受BBC中文采訪時指出,ADHD的特征是執行功能的障礙,這可能影響需要組織、優先排序、集中注意力、調節情緒、管理沖動(選擇最符合情境的行動而非隨機反應)以及記憶和處理大量信息的日常任務。
ADHD雖然是一個只會影響工作效率和生活邏輯的一種心理障礙,但在追求高效、高分數的中國社會,這幾乎是一個寫上簡歷就意味著失業的瑕疵。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在今天的中國語境下,它出人意料地成為了Z世代之間流行的標簽,離開了病理化的闡述背景,成為躺平、摸魚、反對內卷、追求獨立個性自我的一個連鎖詞匯。

就像王寧所刷到的社交媒體影片一樣,一些博主開始自發科普ADHD,從臨床表現到用藥都有詳細介紹——這種詳細的科普很快轉化成為新的網絡熱詞。在小紅書上,ADHD直接相關的帖子有兩百多萬條,相關聯的帖子還包括「ADHD自救」,「ADHD症狀」,「ADHD調整」等,分別都有數十萬條帖。
ADHD和在中國才流行起來的MBTI16型人格測試類似——這是一種心理分類分析法,在過去幾年裡,從韓國到中國,很多Z世代年輕人都在用四個字母排序來介紹自己,恨不得印在身份證上。「ADHD」這個心理障礙被抽象簡化為一個名詞,在眾多社媒博主的影響下躋身其中,成為了一個流行的自我介紹詞匯。
「我叫王寧,是一個enfp(MBTI分類中的一種人格類型,代表著外向E、直覺N、情感F、感知P的特質),」王寧說,自從她知道ADHD之後,她逐漸開始直接這樣介紹自己,覺得這樣可以更快讓陌生人了解自己。
「大家都知道enfp是什麼樣子,ADHD現在也很火,大家也知道,這樣如果我再前後無邏輯發言,或者突然神游,大家就知道這是因為ADHD而不是我沒有社交禮儀。」
由於社交媒體上常見的ADHD形象往往和一些活潑且人氣很高的生活類博主深度綁定,談及ADHD,中國民眾的普遍印象是:思維活躍,「很有活人感」——這反過來也是ADHD快速走紅中國互聯網的原因,它顯得無害、甚至有點可愛,無傷大雅地增添了很多快樂氣息。
和ADHD一起綁定的還有迅速躥紅的輔助注意力集中玩具。
這些玩具大多是通過佔用買家手部動作,通過轉移注意力來強制實現注意力集中。這些購買鏈接動輒有上千單交易,玩具的價格也從十幾元到幾百元不等。

楊欣在接受BBC中文采訪時表示,ADHD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特殊類別,即便是沒有診斷的人也有可能體驗到ADHD的症狀——在新冠疫情後,多項研究表明,缺乏專注力這樣的ADHD臨床表現在大眾裡變得更為普遍。研究還表明,智能手機等屏幕使用時間與注意力缺陷之間亦存在相關性。
ADHD有三個主要類別:分別是無法集中注意力、多動或者過度活躍、或者是兩者的結合體。
在澳洲,ADHD是「神經構成多樣性運動」的一部分:每一個人的大腦結構生而不同——在幼兒教育上,認識ADHD是一種必要的因材施教手段。澳洲積累了300多項臨床心理障礙診斷,ADHD受到了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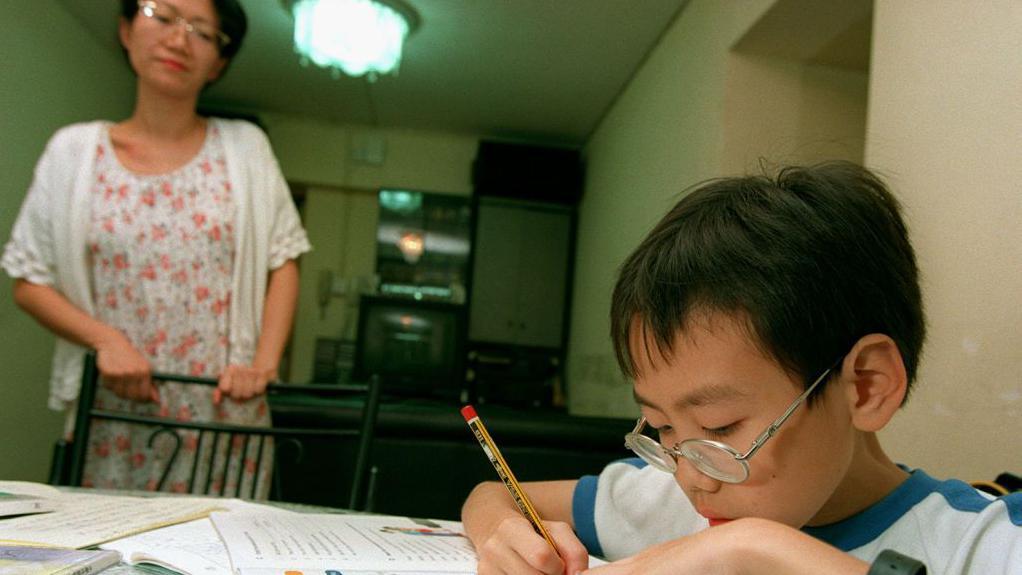
楊欣指出,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有關ADHD的討論,很好反映出社會對於心理健康認知的提升。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中國和澳洲也就是廣義上的國外用的是兩套系統,中國的系統裡是沒有ADHD這個東西的,這個詞能走紅,我能想到的第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民眾不願意再去服從集體主義,開始追求個人的自由。強調思維多元的ADHD就成為了這個趨勢下最顯學的存在。」楊欣這樣說。
王寧來自一個中國中部的縣城高中,這個學校亦曾效仿瘋狂追求高考成績的衡水中學模式。王寧高三那一年,校方給每一個教室都安裝了監控攝像頭,並在學校門口放置了巨大顯示屏,邀請學生家長隨時來監督自己家或者別人家小孩的在校情況。第幾排第幾座在課間休息時間吃零食這樣的事情如果被監控室的保安、或者某一個學生家長目擊的話,這個學生會被廣播全校通報批評。
這個巨大的監控直播設置在縣城裡收獲了普遍好評——學生的成績確實有提高,盡管關聯因素並不可追溯。
走出校園後,她進入一家國企,雖然沒有大廠那般過度加班,形式化的活動只多不少,她一度懷疑自己生活的意義:才26歲,過模版人生,行將就木。
王寧說,那幾個博主的影片喚醒了她的一些記憶——ADHD被當作一個出口,承載了很多中國Z世代年輕人無處抒發的浪漫幻想。在小紅書上,一些用戶親切地稱呼ADHD為「小貓在草叢裡追蝴蝶般的思維模式」。在追求就業率、追求正確、追求復制和進步的中國職場環境裡,坦白說「我有ADHD」和坦白「我可能沒那麼好管理」直接畫上等號
中國民眾將ADHD的語境幾乎僅限定在工作場合。「在家休息的時候也沒有人會去考慮做完A是不是要立刻做B以提高效率,只有職場是這樣。」王寧說。
她在北京積水潭醫院做完了檢查並完成確診、拿到了幫她提高專注力的藥物,並不停問醫生ADHD是否會「留檔」——在中國,精神分裂、分裂情感性障礙、偏執性精神病、雙相情感障礙、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等六種疾病被要求留檔管理,抑郁等疾病亦有一定概率進入個人檔案,在未來的某一天可能影響本人就業等社會活動。
王寧說,盡管她吃藥後不久,因為藥物的副作用有加快心率一條,她感到身體不適於是立即停藥,在確診單到手的時候她還是感到「很欣慰」,因為這意味著她的跳躍性思維並不是她的錯,而是「大腦生而不同」。
楊欣亦肯定診斷本身對於ADHD群體的作用。
「對於個人而言,這種廣泛討論本可以成為他們身份認同的缺失拼圖,或者一種解脫感——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自我確診可以讓他們把生活裡的一些挑戰解釋為大腦的自然變化,而不是『這是我的錯』、或者『我沒有努力足夠多』,」楊欣說,「還能幫助他們形成一個社群,更有利於去構建一個包容和有同理心的社會。」

此外,楊欣指出,ADHD這個概念的快速走紅,也意味著中國民眾過於迫切尋找一個「全合一」的生活萬能解釋——這有一定概率是在掩蓋他們生活裡真正的問題。
「ADHD始終是一個西方式的概念,是在西方定義框架下的診療,它能多大程度適配中國體系下的個體經驗?這裡要畫一個問號,種種心理障礙都不是一個原因所導致的,它們都是綜合作用的產物,」楊欣說,「而且,對於所有的心理診療來說,診斷本身只是第一步,並不是終點……你有ADHD,然後呢?」
一些中國民眾很自然的下一步跟王寧一樣:吃藥。
李女士供職於上海的一家律所,長時間的案頭工作並不允許她有太多時間付諸個人情感或雜亂思緒,效率是她留在這裡的唯一依憑。在前往醫院確診之前,她已經知道了自己「十有八九就是ADHD」,而且她很清楚,通過生活方式的調整來矯正ADHD幾乎不可能:她是一個律師,沒有時間這樣做。她需要最直接的藥物。
針對ADHD的精神類藥物在中國受到嚴格管控的,需要通過醫院門診才能獲得——但是,由於中國成人ADHD診斷啟動過晚,能給成年人進行診斷的門診數量非常有限,像李女士這樣有明確開藥需求的人就會陷入困境:什麼時候才能請到假、掛到號。猶豫再三,李女士最終是在兒童精神科完成了確診和拿藥。
在請假去開藥之前,她先依照小紅書的提示給自己購入了一個ADHD輔助專注玩具:一個莫比烏斯環形的塑料捏捏。僅在她下單的那一家網店裡,這一件產品即已售出6萬單。
李女士坦言自己很擔心沒有幫她完成專注的藥物的話,情況要怎麼辦。
「我沒有時間去系統性地處理我的問題,我需要長期專注,我知道專注不了不是我的錯,但我是個律師,我需要專注,」李女士焦慮地表示,「今天我可以靠買這些捏捏緩解,明天要怎麼辦?我怎麼會工作到沒有時間去面對我自己的問題呢?」
本網頁內容為BBC所提供, 內容只供參考, 用戶不得複製或轉發本網頁之內容或商標或作其它用途,並且不會獲得本網頁內容或商標的知識產權。
17/10/2025 05:00PM
17/10/2025 05:00PM
17/10/2025 05:00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