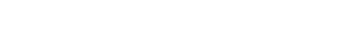 中文
中文

2020年春節以來,胡安六次前往香港看電影,雷打不動地,每一次訪港他都要前往油麻地電影中心巡訪,看看有沒有新片,買票坐進去,五年以來,作為一個常居長三角的人,他在香港的電影院裡共集出八十多張電影票根。
「有機會能看到一些平常無法在電影院上映的電影我定是不會錯過這種機會,」胡安這樣說。
和胡安有同樣想法的觀眾並不少,在中國電影愛好者聚集平台「豆瓣」、以及生活分享平台「小紅書」上分享前往香港看電影的經驗。「小紅書」上的「香港電影」這個話題,被前往香港看電影的討論所佔領,截至目前有150多萬條帖文,7.84億瀏覽量。大部分帖文都在近半年產生。
電影從業者亦對BBC中文表示,行業內早已注意到今次大陸觀眾跨境看電影的熱潮。
小紅書上,甚至有影迷專門為跨境到香港看電影的影迷群體免費制作票夾,上面寫著「乜大陸冇電影睇咩?」,背面則印刷一個巨大的「有」字,配合一些影射中國電影審核制度的「鬼才知道為啥要有特供情節的《詭才之道》」。
正反兩面的自嘲來自長期流行於中國互聯網的電影市場迷思。「乜大陸冇電影睇咩?」來自2023年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一則趣聞。當時,一個影迷在豆瓣上記錄說,她丟失了港澳通行證,於是前往警署報案。警察問她來香港幹什麼,她說看電影。警察遂難以置信地問:「大陸沒電影嗎?」
這句質疑快速躥紅中國互聯網,轉載此條趣聞的微博帖文就收獲近七萬條點贊,「大陸沒電影嗎」這個詞條至今依然存活,到今年7月還不斷有新帖貢獻到此詞條下,嘲諷由於分級制度缺失、審核制度的長期存在所導致的中國電影市場萎縮——這個並不是體量不大,只是由於選擇缺失而導致畸形坡腳的古怪市場。
還有票夾上寫著中國導演婁燁提出的「二流觀眾——他們根本看不到應該看的東西」——這句話被文藝愛好者廣泛引用,用以影射中國電影創作者在追求藝術表達和過審之間搖擺的境遇、審核制度以及分級制度缺失之下所導致的觀眾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今年中國在《哪吒2》上努力造勢、多次延長其在映時間以爭取更多票房以創造一個奇蹟,這兩年中國電影的票房依然大跌,整體票房非常平淡。
以中國影視行業比較注重的國慶檔為例,據燈塔研究院數據,今年國慶檔以18.35億票房收官,日均票房2.3億元,平均票價36.64元,近五年首次降至40元以下。從近十年的數據來看,今年國慶檔票房僅高於2016年的15.9億元和2022年的15億元,與高峰期,即2019年的44.7億元對比下滑明顯——即便有經濟背景不好的影響,亦難掩院線內容匱乏帶來的票房疲軟。
這幾個票夾忠實反應了前往香港看電影的大陸影迷心情:他們希望在香港彌補在大陸影院所無法做到的自由觀影以及更好的觀影體驗。

此前BBC中文就有報道,2019年初起,撤檔就成了高懸在中國影視行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業內人士叫苦不迭,指審核制度從劇本立項即開始介入,公映許可證發放到最終上映更是層層加碼,每一步審核關卡都越發嚴格。撤檔、不過、再改,這些折磨整個影視行業的手法讓中國本土的影視行業戰戰兢兢:畫面不能有紅色的血、不能有大量裸露畫面、髒話需要剪掉、要去政治化。
中國影人製作影片送獎海外電影節亦難逃審核。
引進片的情況也並沒有更好。對於中國觀眾來說,一個海外電影從制片發行公司選片、進口、到上銀幕見觀眾之前同樣需要經過審查、獲得大陸電影公映許可證,即龍標——在配額制度下,中國電影局每年允許引進放映的進口片本就數量有限,影視公司、發行公司為了保障自己的收益,會在數量限制下優先引進叫座動作大片,這導致中國觀眾在電影院裡能接觸到的引進片種類就極為受限,還有一定概率是剪輯版。
審核制度貫穿在大陸放映的所有影視,即便是產於半個世紀前的老片依然難逃送今日之審核體系的命運。
2007年,斬獲當年威尼斯影展最佳電影的三級片《色,戒》上映,和香港觀眾所看到的完整版相比,大陸公映版刪去了7分鐘裸露劇情。為了觀看完整版《色,戒》,根據BBC中文當年消息記錄,大批大陸觀眾在國慶黃金周期間湧向香港。
這樣的跨境觀影潮在20年後重回市場。
除了經典文藝片、如最近的大衛林奇常規放映、亞洲國際電影節放映之外,《鬼滅之刃》、《鏈鋸人》等被大陸觀眾戲稱為「不可能在中國上映」的商業片亦吸引很多中國觀眾專程前往香港觀影。
今年8月起,在抖音、快手、微博、小紅書上,分享如何在香港影院購票觀看《鬼滅之刃》的貼文動輒收穫過千條互動。「去香港看更多電影、去看自己愛看的電影」逐漸成為部分中國觀衆的共識。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吳國坤對BBC中文表示,這樣的跨境觀影活動在香港這座電影城市一直都有發生。對於大陸觀眾來說,影院的選擇並不多,來香港參加電影節或者特別放映在跨境越來越便利的情況下會更為常見。這樣的觀影行為亦有利於反哺電影產業。
過去兩年時間裡,香港逐漸出現影院倒閉潮,小型放映空間亦在縮減。2021年,港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引入國家安全的考量因素,《時代革命》、《憂鬱之島》等片亦因為這個考量無法在香港影院裡與觀眾見面——但依然,對於苦大陸院線電影審核、配額制度之久的中國觀眾,香港依然是他們最近的熱愛之選。
在接受BBC中文采訪的大陸跨境影迷、以及小紅書的討論帖子裡,「有觀影氛圍」和「選擇更多」是影迷最常強調的兩點。
胡安說:「即使香港新的電檢制度上路,香港能上映電影的種類、尺度都是中國內地電影院無法比擬的。即使考慮到我在內地參加過的那些節展,他們仍無法媲美香港電影節。比如許鞍華的《詩》,在中國的放映機會寥寥無幾,即使同為內地電影,萬瑪才旦的遺作《雪豹》在香港電影節上映的應該仍是更接近導演意圖的版本,字幕為繁體,觀影時就能明顯看出內地版本將會做哪些改動。」
此外,胡安多次強調他覺得香港發行和出品商在選片上「很有品味」,電影節俱樂部周末常規放映、電影策展都有不錯的表現,對於影迷來說是很好的體驗。
肖張是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在學校期間,他五次專門為了看電影前往香港——一個小時的車程,對於他來說完全沒有壓力。他會挑選放映更集中的時間段前往香港,比如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或者百老匯電影中心的德國電影周、LGBT電影節、亞洲電影節或者法國電影周期間趕往香港。在他的印象裡,哪怕是抵達影院後再打開購票窗口,也總會發現有他想要加入片單的新片上映——對於大陸觀眾來說,這是完全無法想象的「自由電影海」。
「以前我專門去北京電影節,想去搶《悲情城市》,你加價找黃牛都搶不到,但在香港,人家每周都放映。還有許光漢的那個《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一個男同片,你都不能想象在大陸上映,更不要說在銀幕上看,但你只要一到香港,買張票就進去看了,」肖張說,他回憶在一次入境過關的時候,海關工作人員把他攔下填問卷調查,其中問到他來香港的原因是什麼,選項中「參加文化消費、電影節等」,肖張說那種作為影迷「被看見、被賦權」的感覺無法比擬。
實際上,香港政府確實在推動發展電影旅遊產業,根據地方媒體報道,在2019年和2024年,香港政府分別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10億和14億港元。
「愛看電影這件事居然是政府在支持,他們在認真幹、很重視啊,」肖張覺得很驚訝,自嘲稱自己在大陸看這些電影頗像「過街老鼠」:找不到片源、有「看盜版」的道德壓力,還容易被另類眼光打量。
胡安說,在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他連續兩年向主辦方反映同一個問題,但至今仍未改善。他還曾多次遇到不專業的放映:上影節的一些場次在不提前通知的情況下,延遲一小時放映,片方也沒有任何解釋。
肖張亦盛贊香港作為電影之都給影迷創造的觀影空間。他很喜歡購買電影節周邊,在香港,他不需要像在大陸一樣先顧忌「這是否政治敏感」、「能否出街(佩戴出門)」,從帆布包到印章,專屬於影迷世界的台詞語錄、海報、小像均有,每一個電影節展位和影院附近都有官方售賣——他笑稱「總算沒有版權壓力在了」。
回憶此前在上海念本科時,肖張也曾奔波於上海國際電影節:但如今票價逐年上漲,如今均價已經在90元人民幣以上還沒有優惠;各個電影院之間相隔甚遠,影迷需要花很大力氣安排時間通勤趕場——這些在香港都並不存在。
「在香港買票,我都不說學生票20塊錢有多麼優惠,就算不是學生,大額購票也有可觀力度優惠,這些我在大陸都不會遇見,在這裡,你感到自己是一個平常影迷,而不是被市場虎視眈眈的韭菜,」肖張這樣說。回憶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他購入18張電影票,折後僅花費六百元人民幣左右——如果是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這個價格僅夠他購入五張電影票。
胡安還指出,他認為內地的院線和節展是個系統性的問題,供給側無法提供好電影或者發現一次次被騙,自然觀眾就不想進電影院,影院賺不到錢電影院就會缺乏維護,觀影體驗就會越來越糟糕。
「人們確實有娛樂的需要,所在的環境讓大家不太願意考慮別人的感受。在中國電影院裡看電影這件事情真的和新聞自由、審查制度、電影分級等一系列積重難返的問題相關,我對短期之內有什麼改善不太抱希望。」
其實在專程趕赴外地看電影之外,大陸影迷在疫情後面對並不多元的院線選擇,逐漸有了另一種選擇:地下放映。具體表現為一個地區的影迷聚集起來,十幾人到上百人不止,他們聚集在咖啡店等公共空間、甚至和地方影院進行合作,小范圍播放大家喜愛、且在大陸院線難以播出的影片,比如謝晉導演的《芙蓉鎮》、婁燁導演的《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小津安二郎導演的《東京物語》等。
胡安亦對BBC中文表示,疫情期間,他也有參加一些觀影團的活動,自己也曾組織過觀影團,疫情期間曾有小范圍播放《詩人》、《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之類。
最初,這些小觀影團氛圍極好,大家互相用熱情帶動、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對於胡安來說,這些小范圍的觀影活動給一些無法在大陸發行的電影一個見到更多觀眾的機會,對於觀眾來說也很必要——如果沒有這些觀影團的存在,觀眾們只能在當季並不多的熱門電影中選擇自己並不那麼想看的片子。
這些電影愛好者自留地亦讓胡安結實志同道合的朋友,哪怕是觀影團活動結束之後,他們依然保留了良好的關系往來。
「這些朋友讓我更了解電影,帶我更了解電影史和影史上的那些重要導演,能和他們一起討論電影,我覺得我確實運氣不錯,」胡安這樣說。
但不久後胡安意識到這些小范圍觀影團缺乏管理且「烏煙瘴氣」,君子游戲終難長久。胡安回憶,曾有同行將小觀影團行為舉報到電影局,互相扯皮:一些人指出某個觀影團虛假宣傳、 拒不退款;一些人指出某個團團長為人不行。
更之後,商業行為開始湧入,各個觀影團之間開始利用不同的周邊、或者贈予的周邊數量來吸引觀眾,這背棄了觀影團同好交流分享的初衷。此外,藝術聯盟放映站的地方站長、或者imax粉絲團的團長等競爭去和更接近行業的「核心人士」社交,嘗試去獲得更多正版周邊——這樣的競爭讓他覺得有些厭倦。
「但不論如何,這樣的觀影團仍然集中在一、二線大城市,以及觀影團越來越多,競爭也越來越激烈,」胡安這樣回應。
在北京、上海、蘇州等地建有電影資料館,常規放映修復片,對於很多大陸影迷來說,這是不可或缺的日常「精神補給」。
肖張也在這些資料館的粉絲群裡,他極為經常看到管理員要求「不允許出票給其他人」、「僅限本人」參與等,強調不允許外賓出現、也不允許在社交平台公開放映關鍵信息「如組織方」。
肖張笑說:「放電影搞得像地下黨接頭。」
但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這樣小規模、小心翼翼的觀影放映活動,依然非常限定於資深影迷之間,為了規避審核、逃避「被查」,普通民眾非常難以得知這些放映信息,放映方也對普通觀眾持有懷疑態度。即便僅在一線城市才有像樣、成規模的地下放映,這些影迷群的身分審查依然長期存在——即便是為了避免被舉報。
那麼對於更多大陸影迷來說,去香港直接購票看電影,是難以被取代的、更自然的選擇。
但對於香港來說,《國安法》的出台對於放映來說也是震攝——關於本地、中國持有批評意味的影片亦難再進入影院,觀眾可以在影院看到關於全世界所有政體的議論、紀錄、對暴行暴政的控訴、對惡政的批評,但唯獨不會看到關於本地的討論。這種晦澀隱忍的態度亦逐漸蔓延到香港影院。
2019年之後,紀錄「反送中」遊行的影像資料頗多,亦吸引大量大陸遊客觀看——只是和大陸場景相似,這些影片亦只能通過地下小規模放映的形式與觀眾見面。近六年來,香港的審核制度逐漸加強,昔日輕易能租到的放映場地變得稀少,關於這些影像資料的放映從地下轉為更地下,甚至絕跡。
吳國坤指出,香港在70年代時即有一些非官方的民間放映、觀影組織出現,後來逐漸演變為電影制作小組等,他們去拍攝了一些獨立電影,拿去參加電影節,這在當時是一股風潮,吳宇森導演亦曾參與這些非官方組織——對於香港來說,這些放映會極大促進了本地的電影發展。
吳國坤還提出,在影院觀影的體驗對於影迷來說是無可替代的。這不僅是一個無干擾的電影欣賞環境,觀眾可以完全進入電影的世界。如今,影院還提供了一個體驗式的過程,讓影迷完成了從個人到集體的轉化過程,一個人進入集體參與了觀影活動,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種離開自己的手機、電腦屏幕,重新回到大眾的機會。
胡安也表示,如果是在家看電影,自己會忍不住去按暫停、然後去做點別的事情。但是在影院裡,播放這個行為無法被打斷,精彩的電影一次性放完,他能感受到電影制作人的心路歷程和脈搏。
肖張會去影院再看一遍自己看過的經典電影,因為「銀幕的感覺是沒辦法被替代的」。他還認為,影院這個空間本身對於影迷來說就是一個「神龕」,只有在一個尊重電影的地方,才能不斷吸引熱愛電影的人加入、來來往往。
他曾在香港電影節期間遇到許久未見的朋友,收到別的陌生影迷的小禮物饋贈。
他記得一次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一個白發長者坐在他旁邊的座位看了不到20分鐘就離開了。散場時他在門口再次遇到了這個長者。
「我才知道他可能是坐在樓梯上、或者站在門口看完了全場,因為再走進來就要打擾到別的觀眾了。在影院,你能感受到大家在互相尊重,這種感覺是無法比擬的,」肖張這樣說。
此外,肖張明顯感到在香港的觀眾普遍更「尊重銀幕」。遲到、接電話、睡覺、攝屏等常見於大陸影院的行為在香港甚少出現。
每年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位於上海的觀眾都會被遭遇「出警」事件的影院素質震驚:有觀眾將咖啡直接倒在遲到觀眾頭上,還有人因為有人小聲交流而去肉搏「教訓」對方——胡安曾多次遇到不文明觀影、以及為了制止不文明觀影行為而大打出手、最終亦影響全場觀眾的行為。
「在香港看電影也不是完全不會碰到不文明行為,一來會有工作人員主動紙質,二來我沒碰到大聲出警的情況,我碰到唯一一次是有人狂拍前面的人凳子,叫他不要看手機了,」胡安說。
本網頁內容為BBC所提供, 內容只供參考, 用戶不得複製或轉發本網頁之內容或商標或作其它用途,並且不會獲得本網頁內容或商標的知識產權。
05/11/2025 05:00PM
05/11/2025 05:00PM
05/11/2025 05:00PM